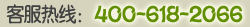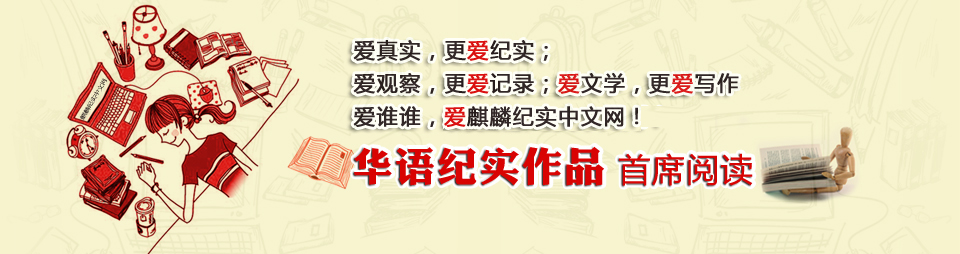亡灵叙事与深度文化反思(雷达)
发布时间:2012-09-27 14:57 作者:雷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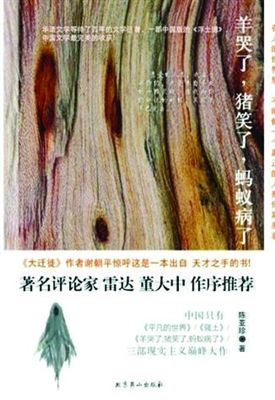
一
读完五十万言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我不想掩饰我的震惊。我预感到,作者陈亚珍有可能、或者已经创造了文学的奇迹。虽然曾与她有过一面之缘,虽然我读过她的一些作品,包括质地很不错的小长篇《十七条皱纹》,但是面对《羊哭了》我依然有不可思议的感觉。我惊异于,她的灵魂思辨的犀利与滔滔不绝,她在艺术表现上的大胆与叛逆,尤其是,她对中国封建的节烈与假革命之名义的节烈对于中国乡土女性的荼毒,对历次政治运动对人性的伤害之深,以及对属于中国经验的、渗透到民间底层的政治文化形态的反思,应该说都是独特的,罕见的。她似乎是与我们津津乐道的所有女作家都不一样的一位女作家,她基本没有进入过研究者们的视野。但她是雄强的,她是沃野上的一棵大树。
作者借亡灵叙事的技法讲述了叙事者“我”死后二十年,灵魂重返人间,寻找未曾获得的人间亲情、人世伦常,并以此来反思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思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英雄膜拜、革命情结、男性权力、女性伦理等等,是如何改变和重塑了特殊年代的人们的情感和道德。
作品的叙事聚焦于一个由民间伦理维系着的村庄——梨花庄,怎样被战争、传统道德、以及人的欲望所毁坏的过程。它也通过梨花庄这一具有传统意味的空间的存亡,隐喻一个民族深重灾难的根源和在当下困境中的突围之难。对于这样一个极其“重大”话题,作者究竟是如何通过她的一批女性人物和一个小村庄来承载的?她的讲述方式和价值立场在当下中国文学序列中的意义何在?
二
作者的讲述方式和价值立场之独特首先在于亡灵叙事的选择。所谓亡灵叙事,简言之,就是一种以亡者的灵魂为视角展开文本叙述的行文方式。在中国文学中,鬼叙事、亡灵叙事或者死亡叙事等“非人”的讲述方式并不是主流,但相关的作品倒也不少。亡灵叙事或阴阳两隔间的对话方式,与基督教传统中的魔鬼、上帝、子民间的对话是有本质的文化差异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两重天,阴间是恐怖的,神、鬼、人各司其职。凡人肉体死亡后的冤魂、厉鬼与活人的对话多隐含着对人世的眷念或怨恨。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教)中,天堂是极乐的自由世界,俗世与天堂并不对立。所以,阴阳两隔间的亡灵叙事及其眷顾、怨恨主题是中国文学、文化的特征性符号。白居易的《长恨歌》,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即以阴阳两隔的情感倾诉表达男性对女性死者的追忆。到了中国的叙事文学形态逐渐成熟之后,这种叙述和表达就更为多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多以“人格化的妖”与孱弱书生的爱情悲喜剧来结构故事;《红楼梦》中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则以宝玉“亡灵”的身份提前批阅了金陵十二钗的前世今生。无独有偶,山西女作家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则是一部沉甸甸的亡灵叙事。作者以“我”——仇胜惠的幽灵的视角,讲述了她短暂一生如何走向死亡且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和经历,同时,通过她的遭遇审视了一个村庄、一群女性、一个民族的悲剧性命运。
三
首先,小说叙述主体是女性,立场是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在作者的讲述中,“我”的身份扑朔迷离,与父亲和“祖根”的血缘、亲情是“我”一生的困惑和憾恨。这使得“我”的寻找和渴望接近“父亲”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讲述过程。作者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了“我”(胜惠)的出生。胜惠出生于“抗战”爆发的一天。花蛇像梨花庄的守护神一样警告一场灾难的到来,但蛇的出现也促使了“我”的早产。胜惠本应该生在马年,可因为母亲被蛇惊吓,使她提前在蛇年降生。自从“我”降临人世后,那条花蛇就不见了。所以,“我”的出生被奶奶指认为“花蛇转世”。这本来是只有奶奶和母亲知道的天机,但它很快就被泄露了。起初,胜惠的身上有一股神谕般的力量,她的喜怒会决定梨花庄人的福祸,自然就带有神气和妖气的双重性。在战争年代,她成了全庄人心目中的“神”。因为,胜惠的父亲带着全庄三十多个男性去“抗战”,女人希望胜惠的灵性为她们的丈夫保平安。当男人们阵亡的消息一个个传来时,她又被认为是比蛇蝎还毒的“妖”和不祥之物。因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被胜惠父亲带出去的“兄弟”们几乎全部阵亡了。梨花庄三十多个女人成了寡妇,而只有胜惠的父亲混全回来,且后来当了“大官”。那些女人们怎么会不怀疑胜惠作为蛇妖的自私和狭窄呢?可是,胜惠对自己特异的“功能”全然不知,所以只能承受这“残酷的善行”。她曾跪在五道庙里为每一个出征将士祈祷,祈求平安。但是神意并未按照她的祈祷和心愿发展。那么,胜惠到底有没有这样特异的能力呢?正如她奶奶说的:“娃身上的精灵到底有多少呢?”故事的悬疑由此不断展开。
在选择女性视角时,作者有意强调一个女性偶然的强大“功能”,同时又回避了宏大叙事。这使得女性“功能”的偶然性带上了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尽管整个故事发生在战争、革命、社会剧变的大背景下,但对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作者尽量作了虚化的处理,甚至直接让历史退到故事的后面,在这个背景下,以“我”———一个女人死后的灵魂来讲述另几个女人的故事。因为故事不在战争的正面,而在战争的背面或侧面,这使得“我”能够随意出入故事。“我”几乎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推动故事的核心人物。
这个全知全能的视角与叙事者的身份密不可分。因为“我”是胜惠的灵魂,所以可以幻化为各种观察者;也可以自然、自如地变换视角,比如幻化为萤火虫、护庄狗等身份观察,这就消除了限制性视角带来的局限,对其他女人的讲述也就能够自然地纳入叙事的合理范畴。
作者以这一视角讲述了梨花庄两代女性的遭际和命运。第一代女人是像胜惠母亲一样,为了民族的独立,离别了丈夫的一群。第二代女性是胜惠和那些被父辈英雄的光环感召的烈士子女(男性多为配角)。但似乎每个女性的命运都与“我”(胜惠)纠缠为一个“死结”。这也是她的死亡成为秘密的重要原因。在第一代女人中,“母亲”因为答谢蛇神九斤对“我”母女的救命之恩,无奈而又不无情愿地将自己身体交给九斤作为对他的报偿,这种“大逆不道”使她成为梨花庄的千夫所指的“荡妇”。“英雄父亲”以一纸文书很体面地休了她。母亲“偶然”地失去了成为“县长太太”的可能(是否也是必然?),更受到了别的女人的最大的挖苦——“天生就是当 ‘破鞋’的命”。其他女人也开始把对丈夫的思念和生活的孤苦感受全部发泄到“我”和母亲兰菊身上,这是一种“必然”。“我”只能在养女和亲生女的身份中寻找真实的自己。
四
第二代女性的长大成人时期是在“解放”后。作者主要把这一代女性放置在建国初期的生产建设到“文革”极左这一段时期。老一代女性对“我”父亲的革命精神和大公无私表现出极大的崇拜,包括母亲,她一直以无言的方式牵挂他的身体、地位、荣誉,对自己的“被弃”也从没有任何怨言。而第二代女性,在英雄故事中入眠,在烈士亭子边上长大。她们身上隐藏着强烈的革命、反叛精神,她们复仇的欲望一触即发。当“我”的父亲仇二狗揭露了“大跃进”的荒谬后,被定为“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的“右派”,之后被红卫兵(第二代子女)以“杀人犯”之名判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而与胜惠一起长大的烈属的女儿玉米,在胜惠父亲当上县长时,剥夺了胜惠对父亲的“拥有”权,并给予其谋杀烈属的罪名。她和“我”(胜惠)相好的男人天胜定了婚,“我”独吞苦果。进城后,玉米设骗局抛弃了天胜,又把拆散婚约的罪责巧妙的强加于“我”。而被权力压抑的张世聪———“我”父亲的秘书,见风使舵,在父亲身为县长时,乐意地接受了父亲的“安排”———与“我”结婚;当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他反戈相击,假以“我”的名义与他共同揭发,使“父亲”的罪名成为“铁的事实”,然后匍匐于玉米的暴力下,并以变态的兽欲折磨“我”。父亲得到平反后,张世聪也以“被害者”者的名义平反,当上了法院院长。我却死于丈夫(无意中打死)的一块砖头,“终于,我陪伴着那个孤独的我自己,没有雷声也没有闪电,就像天空无言的流星,默默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结”。张世聪表现出了虚假的“深情厚谊”,他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目;而“我”曾在此之前因身份的模糊,被误解、饥饿等原因多次自杀未遂,在生下两个孩子后,准备为了孩子,像畜生一样活下去时,却变成了孤独的灵魂。但是“我”“揭发”父亲的事实没有得到核实,更没有得到父亲的宽恕,也没有得到母亲和梨花村人的原谅。“我”纠结于两代人身上的“死结”,特别是两代女性身上的情感的盘根错节,没有在人世解开。“我”孤苦无告的灵魂(更像冤鬼)成了“无祖鬼”,以一粒浮尘与母亲和父亲在另一个世界相遇,与天胜在死后心心相印。亡灵叙事和女性视角的批判意义也因此而自然而强烈的显现出来。
五
当我们理清了作品中两代女人的情感历程后,自然会有这样的疑问:历史沉重的包袱一定要完全压在女人瘦弱的肩膀上吗?作品中女性的命运到底在何种意义与民族的命运血肉相连?作者又是如何将二者作出了合理地对接?
首先,作者巧妙自然地以反讽的手法,表达出对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女性伦理进行了深度审视,进而对传统道德对女性的精神钳制作出有意味的反思。梨花庄,这一带有中华民族之隐喻的村庄和书写空间,它“依附在天边的一座大山中,属于太行山的一脉筋骨,从上而下是一条龙姿。村庄的建筑散布在龙头,龙肚,龙尾之中”。从它的诞生和繁衍,选择重情、仁义的始祖梨花女以生命换来了梨花庄女人的勤劳善良,性子刚烈,也换来了梨花庄男性的勇敢豁达、侠肝义胆。这是梨花庄的生命和灵魂。但是不断膨胀的权力追逐和掠夺战争,使梨花庄的生命和灵魂受到了威胁和篡改。梨花庄的女人也像梨花始祖一样在忠主与忠情、有情与无情之间挣扎。但与梨花始祖不一样的是,她们的忠主战胜了忠情,有情被指定为背叛,女性的悲剧性命运也因此一代代延续。战争的无情和男性的欲望将女人变成没有自我的附庸物。抗战爆发后,梨花庄三十多个男人奔赴沙场,三十多个女人的命运又该如何?等待丈夫的焦急,被人引诱的惶乱,丧夫失子的痛楚,性与爱的断裂……当“我”的性命危在旦夕时,蛇神九斤挽救了我,被本能煎熬的母亲,便以身体“偿还”了九斤的救命之债。母亲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选择”。“我与娘第一次达成了撒谎的协议”,但“我”和母亲从此将要面临无尽的悲苦命运。她要抚养“我”长大,守住对丈夫的责任和许诺,所以在自己肚子一天天“羞耻”地长大后,她与三婶“合谋”要在肚皮外“勒死”未出世的孩子。
故事的讲述不断在转折中出现波澜,层层迭起。战争漫长的熬煎并没有遮断世俗女性的凡俗欲望。但作者的叙述明显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女人们在战争的背后谈得最多的是男人,当嗔怨与念想终于换来的只是“烈属”名分时,她们的生活光荣而乏味。所以,在阴阳两界间,本应该阳世最令人留恋,但胜惠的回阳寻祖几乎让她感觉到阳世的寒冷,亲人对他的冷漠,猜疑,之后人世间满街流溢的欲望之水,都让她惊悚;她在梨花庄的贞节牌坊面前,看到了那些“坚强”的女人,被脆弱的“意志”所折磨,也看到了贞节牌坊上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在“我”的回忆中,天胜奶奶在“大炼钢铁”的饥饿年代被“撑死”;获得“贞节”牌坊的女人与最龌龊的男人偷情狂欢;最刚烈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贞节”女人最憎恨夫妇情爱之欢……
从以上富于张力的结构和巧妙的反讽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借胜惠的亡灵的视角来观看阴阳两界,来评判生死两端,从而将问题指向了一个民族面临的许多重大精神问题,即战争与生命,男性与权力、女性与道德,亲情伦理与阶级身份等。作者重点叙述的是梨花庄女性的悲苦命运,以及因此引起的传统女性伦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的挖掘,并通过反讽和抒情加以强化。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思考也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难题:生与死,灵魂与肉体,自我与他者……那么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张力互否和反讽结构中,作者始终具有一种自我审视的叙事态度。正如作者借叙事者所言,“我”开始怀疑:“造成梨花庄的苦难是否也与我有关呢?”梨花庄每个女人的死,似乎都与“我”有关,更与“我”的母亲有关,因为是她阻止了“我”对更多抗日战士的祈祷。她们对“我”和“母亲”的仇恨已经深入骨髓。从这个意义上看,胜惠的难言和苦衷更胜于那些被压抑、熬煎的女性。那么,她到底能承担多少罪恶和苦难呢?
六
从整个文本的叙述方式来看,作者选取死后二十年亡灵重回现实,寻找人世亲情,并以此重现被宏大历史所掩蔽的“死者弯曲的倒影”。正是这一叙事视角的选择,使得叙事者可以以个人的方式进入历史,使个人的感受比被书写的历史本身更形象、更富于感染力。作者的历史感也因此得以突显。尽管作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一直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为背景,但作者进入历史的方式是以人物带动历史,以人物评价历史。比如“大跃进”之于乡村底层人物千百年的精神内伤,比如个人崇拜之于“精神父亲”的权威,再有女性对男性的精神依附等,特别是以一个村庄,一群女性,她们的悲剧性命运与一段段历史的血肉关联。这是叙事者试图解开的秘密。
这部作品的突破之处就在于试图对一个民族秘史的解密。我认为,被民族历史和宏大叙事所遮蔽的民间话语,就是这部小说的叙事秘密所在。正如作品中那些被遮蔽在大人喜怒哀乐下面的小孩子们的脆弱和敏感,也如傻子金宝对嫂子“愚笨”的一往深情一样,在评价历史的过程中,作者把“我”寻根问祖,寻找父母亲情的情感经历放置在那个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语境中,来反观革命、阶级话语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父亲”对世俗亲情的压抑。“我”对父亲的精神依恋和对亲情的渴望总是被父亲“革命不是一家一户,一儿一女的事,而是普天下的事”、“革命不相信眼泪”等集体话语所淹没;梨花村人的饥饿也被久妮“我们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害怕饥饿吗”所吞噬。这样,个人的情感、欲望完全被战争、革命的乌托邦所遮蔽。这也是作者试图要回答的女性生存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批评“小亚细亚国家”,由地缘、血缘组成的“氏族社会”发展到强调解构血缘、地缘的“共同体”,以阶级关系压倒了血缘、地缘关系。这样的“进步”是可怕的。所以,在小说叙事中,阶级话语对个体话语的遮蔽的复杂性也因此显现出来。
当然,正是因为作者选择了自由穿梭文本的叙事者,从而使部分章节中浓烈的女性意识和批判精神过于情绪化,甚至浮泛化,有时叙事的节奏也缺乏有效的控制。作品中有很多情感和价值判断,并不是通过人物形象或人物自身来显现,而是作者借“我”的叙事者身份直接“说”出来,使得人物形象和叙事者带有很浓的说教气息、议论色彩。说教挤掉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弹性; 议论抢占了人物形象的“留白”空间。人物形象的情理逻辑让位于强烈的抒情和理性的思辨,自然就会某种程度淡化了人物形象的感染力。但我又觉得,我的上述看法也许来源于常规,不能说不对,然而,我对小说中大量的思辨仍保留尊重。
统观全作,无论从叙事的角度,还是从女性立场的价值评判,无论是从进入历史的姿态,还是从反思社会、反思政治文化的角度,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 都是十分难得的厚重深沉之作。它通过亡灵视角,观照像羊、猪、蚂蚁一样弱小者们以及“无告者”们的生存悲剧,并从历史的背面进入了历史,反思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及其深重的文化征候。它不愧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的新一轮反思小说的先锋,也不妨看作是新历史主义观念影响下的一块厚重的文学基石。
(《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陈亚珍/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7月版)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zmf.cc/a/353.html
- 上一篇:没有了
-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