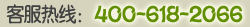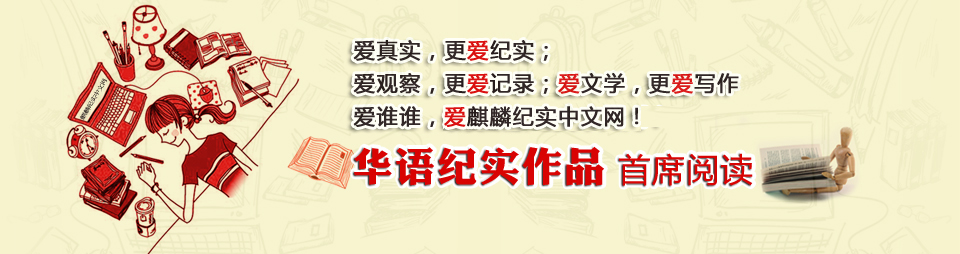张郎郎:一个现代隐士的低碳艺术
发布时间:2012-02-29 10:03 作者:纸磨坊文化
2011年12月30日,著名美术家、作家张郎郎做客纸磨坊文化,畅聊自己文学与美术理念。

张郎郎与纸磨坊文化全体人员合影

纸磨坊文化总裁刘水晶先生与著名作家、美术家张郎郎先生合影

张郎郎先生接受纸磨坊文化采访

著名美术家、作家张郎郎
张郎郎其人
张郎郎,自由撰稿人、喜欢画画。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出生于延安,自幼受父母艺术熏陶,他的父亲为我国著名美术设计家、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
一九六八年他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毕业。同年,他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组织地下文艺沙龙“太阳纵队”是“罪行”之一,9年半后释放。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中国国际贸易》杂志编辑,《国际新技术》杂志总经理,《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华润集团中国广告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曾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康乃尔大学东亚系之驻校作家,同时在语言学系教授汉语,并担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之驻校作家,同时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后又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著有《从故乡到天涯》、《大雅宝旧事》等。
《大雅宝旧事》2004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颇受好评,2012年1月,《大雅宝旧事》由中华书局再出修订版。北京“大雅宝”胡同是50年代中央美院宿舍所在地,众多艺术家聚集在此,作者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本书以儿童的视角,举重若轻的笔法,描写建国初期“运动”中的艺术家们的生活。让人读来泪中带笑,诙谐中见沧桑。
报告文学网(以下简称报):张老师您好,《大雅宝旧事》最近再版了,您能谈谈《大雅宝旧事》里所记录那段故事的背景吗?
张郎郎(以下简称张):大雅宝的故事是发生在特殊的年代,49年后新中国的文学艺术具体怎么做,向何处去,估计中央还没想那么细。当时是让江丰先生负责美术,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服务,这个大方向就决定了。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艺术主流是风花雪月、为艺术而艺术,要把它从那条路上拉过来。加以改造利用。所以,对这些老画家怎么办、怎么用?当时中央美术学院也不知道该具体怎么做。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49年之前像董希文、李可染、李苦禅这些人已经是有成就的艺术家了,但在形势下,要把他们打回到同一条地平线上。重新进入新的生活,做一个新人。这样大家才都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当时对美术也不够重视,才造就了这个空前绝后的艺术巨匠大杂院。也就是这个原因,才让我们这些小孩能住在一起,在一块儿玩,变成了朋友,一起成长。
黄永玉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李可染先生,这篇文章还牵涉进了好几家的故事,都很有意思。黄先生和张梅溪阿姨(也就是黄妈妈)早就有了写大雅宝故事的想法,但可能一方面由于年龄的原因吧,还一个就是他要集中写自己的自传,所以就给搁置了。梅溪阿姨连书名都想好了,可惜一直没有动笔。后来,黄妈妈对我说:“你也可以写啊,从你的角度写。”因为我从57年就离开了大雅宝,观察有限,但是她说,你可以按照儿童的视角去写。这就类似于纪录片的单镜头,就是写:我看、我见、我思。
报:你觉得你写的这本书和黄永玉写过的那篇文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张:我们讲一个院里的故事,他(黄永玉)是从大人的角度,我是从孩子的角度,从两个角度来看,这样就更立体了。若以后黄妈妈有精力再写一本,那就更好了。前几天召开《大雅宝旧事》这本书的发布会,以前大雅宝的孩子去了好几个。他们都说这个想法很好,这只是个开始,以后有条件的话,人们还要继续写下去。
报:关于大雅宝往事您自己也是想继续写下去是吗?有什么打算?
张:对,接下去写就是写我们家的事,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每个家庭他都有大同小异的地方,但是细节却是不同的。(写自己家的事)可能会相对自由些,但是我力求尽量客观,我自己是比较倾向唯美主义的,既不要拔高,也不是解剖的特深那种,意思到了就行了。
报:您创作这本书时的动机只是因为黄永玉夫妇的启发吗?有没有想过是为历史代言?
张:我在创作的时候没有想过为谁代言。我还有本书叫《宁静的地平线》,大概明年出版,它是我的一本纪实小说集。写那本书时,这在我的内心被看成是一次还债,我答应如果我还能活着,我要把当年的故事都写下来。到写大雅宝时,我不是替谁说了,我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很随意。
一本写了很久的书
报:您之前写这本书时是什么背景,在什么环境下?
张:当时我一直在海外,在大学里教书,实际上在美国工作比在中国紧张得多,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正好当时是我生病了,就开始写,把内容都凑到一块儿。今年暑假我退休了,所以才敢答应出版社把这些书慢慢写完。
报:你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写了很久了,这是怎么一个过程?
张:是这样的,八零年我到香港后,因为当时黄永玉和黄妈妈一直在催我写,当时是就写了一个连载的文章叫《大雅宝胡同的故事》,最早是在香港的一本名为《观察家》的杂志上连载,写了一段时间就戛然而止了。因为当时还不清楚这位说书人如何定位,还没想到用孩子的视角去写。当时,我是完全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去这个故事。这样就有问题了,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价值的标准,你讲的话就有品评的内容,一品评,就会有偏见、有谈不到的,谈不清的,自然会有人不高兴了。当然我不至故意去褒贬谁,虽然你想讲一个客观故事,但是,在你讲述的时候想说某个人“正确”,有的听众就认为是在批评另一个人“错误”了。所谓真实的,有褒贬的故事就会出现问题。你本来以为讲一个故事只是有趣,可后来发现讲一个真人的故事真很难,尤其是很出名的人。人们都有自己的观众、粉丝、崇拜者,你写人家的“趣事”。有时候本人倒无所谓,其他人就受不了了。人们会认为在这种褒贬中,企图拔高自己。
在香港刚写了几张,就有人好心告诉我:你赶紧停吧。后来黄叔叔再叫我写时,我就考虑到“前车之鉴”,于是想以孩子的视角去写,只写小时候的事,那时候我们还没用那些“判断”,似乎回避了一些问题。其实,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都有这个问题,比如说:你们有个很好的想法想和人们分享,是否能得到人们的谅解么,或者你有不同的看法,要和人们探讨,现在开展良性的辩论,很难。
报:纪实文学以什么的身份介入到故事里,打开一个怎样的切口很难的。
张:对,很难。后年下半年我就打算写“太阳纵队”,就是一个诗歌沙龙。写那个就会发生真人真事的问题,就别说别的人了,就说太阳纵队过去的成员,你就得一个个人地征求意见。有些人只要求不写自己的名字,有的人就连他的故事都不让写,这在中国很容易吃官司。有人说最好的办法,就干脆改成小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是很多读者就喜欢看真人真事,他们是小说就不想看了,所以这就是个两难问题。
报:您在这类纪实文学涉及其他人故事时,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吗?
张:我征求他们的意见也不是百分百,只是在内容上征求,如果是纯叙述则不会。我这么写是有原因的,这些年来我一直追随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余英时教授,跟他学习。我看到他这类学者都以严谨方式谈历史,还有像伯克利大学的历史教授魏裴德。他们写的历史故事和我熟悉的中国历史故事不同。他们更重视历史的细节和偶然,我觉得写这样历史故事必须有真实的细节,因为细节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我写故事又不是写历史,自由度比他们还大一点。但这才是有意思的表述。我写这些故事书,就得对自己重新的挖掘,把过去那些遗忘掉的碎片重新捡起来,筛选、组合。
报:你这本书出版之后,书中所提到的相关人物是不是也深有感触,找你去聊聊这些往事了?
张: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增订本,这些增加的内容就是很多朋友看到我那本书后告诉我的,有的朋友说他们家这段故事是可以加进去的,这样我才加进去的,我之前虽然大概知道这些情况,但人家没用授意之前我就不能去写。有的朋友提供了更多更新的照片。
报:我觉得《大雅宝旧事》这本书因为涉及到很多伟大的艺术家,所以对现在很多从事文艺工作的人都会有影响吧?
张:我写的这本书出版后,被书店放在美术史类里。一开始看的读者群多是美院的人,因为这个故事要么是说的他们的家长,要么说的是他们的老师。有些人看了后,就觉得过去没想到还可以用这个视角去看那个年代,那些人!而且因为时间过去很久了,人们在现实中跌打滚爬中,人们幼时的印象就很模糊了。通过这个视角可以用全新的方式去回顾自己的人生,就有新的想法。而且我是学画出身,我写的东西很多内容就可以变成镜头,企图写出散文诗一样的镜头,这些画面对一些艺术的初学者或许有所启发。
纪实,要有自己的取舍
报:我觉得纪实文学的真实性是这样的,不是要多真实,更不是要多么添枝加叶。
张:这方面我想的较多,纪实文学一方面不是纯文学,就不能讲得太离谱,尽量句句话都有根据,故事都有所依托;而且不要以论带事,不要先有个框架去宣扬什么,或者表扬谁、批评谁,这样就会在取舍中,丢掉许多真实感觉。叙述一个人,也不要有太多主观选择因素;另一方面我要明白,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不是呈堂供词不是法庭证词,要求每一句话都要有人证物证。那就没用故事可讲了,文学的空间就太狭隘了。故事本身有个表象、你自己有个反映。你只是去叙述,既不是夸张也不是淡化,这的确很难。但关键在于,这个真实是心理历程的感受的真实性,而且符合心理历程的规律。然后你比较温和客观,比较冷静地叙述下去,尽量把更多的事实记述下来,把你亲身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就很好了。实际上后人只能想象当年的故事,不可能身临其境。
报:您觉得你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或者说写作态度有什么特点?
张:明年大概中华书局还要为我出一本纪实小说集叫《宁静的地平线》,那本书的风格是我以往的风格,与《大雅宝旧事》不同。虽然,我写故事的目标是客观、冷静,零温度、零视角那样写。但当时写的时候还比较年轻,还有火气。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不同了,可以叙述得更自然一些。写作就像做菜一样,过去写的跟川菜一样,辣,厉害,有些人觉得很过瘾。但是现在就有点像炒白菜,可能有人说这本怎么淡而无味呢?实际上真会炒白菜了,这可能是一种进步。毕竟,我们写的是文学,不是控诉书,年轻时很激烈的语言,完全可以不要。但读者怎么看你无法预计,你就不必考虑读者的想法。也就是说等你写完一本书之后,这本书的命运就和你没有关系了。读者自己读的时候,在他那里重生,长成什么样很难想象。
报:在您的写作历程中肯定有过一些对文学手法的探索吧?
张:我是一直在想找这个叙述口气,你自己在写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直在讲故事。现在写的《大雅宝旧事》之后,觉得这种语气比较合适我,以后呢,再怎么写就另说了,不可能是终极方式。
报:我注意到很多故事都是以您家庭展开的?您是有意这样写的吗?
张:对,我也想过,如果完全是一个纪录片,你描写张家是怎样的,李家是怎样,你用一个故事带起另一个故事会更有意思。但是,你得有一个全视角,这实在太难了。不如写自己单镜头看得清的地方写起,这比较偷懒。
报:我觉得这本书在语言上很有“京味”。
张:呵呵,实际上你跟我交谈,觉得我说话说的是普通话,可书上为什么有许多京片子,因为教书的缘故就不得不说普通话。其实在大雅宝的时候,我的北京话还不地道,和李燕都没法比。后来我在北京监狱蹲了近十年,天天跟许多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聊天,无论北京话还是北京文化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不少,学了不少。当然我写的时候也不是刻意地选择大量北京方言,太方言化就成相声啦。
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到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浓郁的北京地域色彩,一个是那个年代的色彩。现在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时间上,你都距离那些故事很远了,这两种特色是很自然就写出来的吗?
张:没有刻意追求,有人说我在外国呆的年头太多了,应该是忘记了,怎么反而更清晰了呢?现在我在北京顶多待三个月就赶紧回去,因为北京太热闹了,去那边反而能静下来,小院里喝茶,三五知己聊天,不断回忆、加深印象。
报:也许是当局者迷?
张:对对,有这个意思。
报:我记得哈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为移民的作家》好像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文学史上挤满了无法亲身回归故土的巨匠,但他们最终凭借作品回到故乡人民的怀抱。
张:明年我会出本书,里面有篇文章,叫《迷人的流亡》,本来是海外的朋友编辑的,邀请每位流亡作家,一人写一篇流亡经历。有些作家写的很苦,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我自己没那么苦,就重点写流亡的迷人之处。但是中华书局出的时候,觉得流亡这个词可能会因其政治含义引来误解,就改成了类似“迷人的流浪”这样的题目。这样比较温和些。
报:更文艺的题目。呵呵。
张:大难不死的这些人写出来的东西,容易犯心理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特容易写成苦儿奋斗记,在写作时就一心想为自己伸冤。如果是在法院,这样做是一定的。现在我觉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只是时间和强度不一样。就像我国佛家说的,生老病死,九九八十一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人偶尔来到这个世界,所有的经历都是宝贵的,就像人在临死前,就是插上管子活着受苦也想活下去。因为人活着就有体验,人死了连体验都没了。酸甜苦辣都是一种味道都是生活的一种经历。如果你是从这种理解去写故事的话,你就不会有祥林嫂那样的诉说,才有可能把你的苦难挖到新的深度。
报:作为一个纪实文学的作者,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纪实文学创作的经验、借鉴?
张:目前我写到这些还比较容易,后面会讲到帅府园旧事,就有城市四清等敏感区域了,故事就不好写了。我的心得就是你不一定用全景式的画面去描述一个事,因为你的目标不是一本《战争与和平》,也不是《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书。我这里只是一个单镜头,因为当时经历过那个时代,你心里呢就有处理这个痛苦的过程。有的你只看了一眼,有的你是听别人讲的片言只字,要讲出那个时代全貌,这是做不到的。我也不打算把每个人都放到解剖刀下,我还不一一能加以品评。我只能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并不是把谁贬低也不是把谁美化,我最终想歌颂的是人性的可贵之点。不打算着重去讲人性残暴的兽性的一面,这一点人们似乎都已经看清了,知道了。美好的东西实在太缺稀了,这是我自己写作的取舍。
中国缺的是精神贵族
报:您这本书里的故事发生在文革前期,或多或少涉及文革时的一点经历。针对那个年代,作家哈金就说,中国19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数百万人遭到迫害,数万知识分子被发配到穷乡僻壤,在那里死去。但从这个灾难里没有衍生出一部经典的文学著作。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张:现在这些还在做文学梦的这些人,为什么不像哈金说的去写这么个故事呢,因为文革前后那大动荡,你用什么角度去描述、什么方式去囊括进来,这是个问题。实际上不光我在找,除了哈金还有写《老井》的郑义,他们都有这个梦,但是他们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方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找到了,是否能驾驭。我就比较有自知之明,知道我对驾驭文字比较有把握,我就先把这本书(《大雅宝旧事》)写了,那个写不了也没关系。但是我和大家一样都希望有这样的作品出现。
报:说起文学创作,每个作家都有创作期的问题,您对自己的创作期怎么理解?
张:我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有文艺梦的人都怕江郎才尽。江郎才尽怕的不是技术,而是没灵感,你要干憋是憋不出来的。我在美院和文学界认识的这些朋友,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创作期,很多人是所谓的闪光灯主义,就闪那么一次就得了,以后再努力也达不到那种高度。而我呢,心里有股劲,觉得自己还行,至少让我这老头心里高兴,也许将来会有人说我最好的一本书也就这本了,最好的画也就这次画展了,也有可能。但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还有劲,还有创作的热情,这让我很高兴。反正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没法估算,就像第五代导演,好像创作期最高点都过了,拍的东西都没法看了。可是这个时代都把你已经给符号化了,你随便弄点东西都有人愿意花钱,这就是艺术商业化悲哀的地方。
报:我觉得创作期问题,作家本人有个定位。
张:对,自己得有个客观的定位。
报:对作家而言,创作不一定只是在高度上,还要追求广度,一个作家在面向世界时,是作品面对,还是以作家本人面对,他也是有选择的吧?
张:对,就像李陀,就是一个文学活动家。还有些作家是在固定风格上不断制造而不是创造。
报:也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作家某一段时间作品很多,年产多少就一定是在创作期了。
张:对。
报:就像书中说的那样,您从小在浓郁的艺术氛围当中长大,这群人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这个里面的影响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坏的呢就是影响我们不能入世。也就是缺乏社会性,生存能力弱。生活中你只关心的是文学艺术,也可能是说是个错误的影响。因为,那时候觉得当官没什么了不起,文学艺术家才是无冕皇帝,要是做个买卖就更不如人。像大雅宝那些孩子,艺术家的梦还没有做完还在追索。有些人说这也很好,一辈子是个梦。我有个弟弟叫寥寥和这个社会没法和谐、没法融入,因为他向往在这个时代非盈利地搞文学艺术,这怎么可能?他现在住在通州,过着很贫寒的生活,和自己的女朋友天天画儿童绘本。有些朋友喜欢看,他就混口饭吃,没人喜欢看他就发给朋友看。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你可以说这个想法很好,很理想主义,这就是我们那帮孩子很致命的一个缺点。就像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学校教书,就想画画、写写东西。我有个朋友,当年住在小雅宝,说了句名言,“去教书的、一直在坚持搞文学的都是二流人才,真正明白的人要么是在商业领域要么是在政治领域”。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占用最大的社会财富。实际上是价值观的不同,实际上你自己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来。中央美院有个毕业生叫赵少若,他说前两年许多画家流行搞的是政治波普,政治波普玩的人太多,都过时了,我们应该弄个叫失败主义——我们不和世界接触,不在乎社会承认不承认,就是为艺术。从他的角度还是商业炒作,能不能炒红那很难说了。
有人说我们这类是现代隐士,当然不是要隐居山野,只是价值标准与时代不一样,而安于自己的生活。
就像我这本书,有人就问我为什么不好好做宣传和营销,从商人角度来看,一点错都没有。可我不是这样想,我现在做的文学与绘画,都是低碳的,不在乎赚不赚钱。有人给我出我就写,前两年就有人找我办画展,我说听说现在都要用钱,只要花了钱才能好卖,可我的画没打算卖出个好价,只是为了让朋友们看看。无论出书还是办画展,不花钱就做,这是因为从小我就有的一个观念。这就是我奉行的低碳绘画、低碳文学观念。要做一个低碳的写作者和画画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一个实际的追求和期望值,你追求的是创作中的愉快。如果这本书你打算出版多少、卖多少,你在创作过程中就得考虑这些。你的目的性很强就算了,做低碳的文学与绘画就不可能赚钱。我说这个不含有批评意思,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但我也有偷着乐的地方——我的意思是你写不出来,不是你没有这个才能,是你没有这个心境。
报:您说的低碳艺术是精神上的低碳吧,其实高碳生活的背后是人们挥霍的本能、无度的欲望在作祟
张:对,是这样。
报:那么您觉得您的书算是畅销书吗?
张:我不觉得我的书是畅销书,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像普通衣服一样,这不是时装,但是一件有品位的衣服。可以慢慢的搁在那,总有人买,这不像时装只卖一阵。
报:我倒觉得这不是时装的问题,它是服饰中不同的门类,比如说有的是帽子有的是袜子。您的作品很可能是帽子,而那些即用即丢的东西是袜子之类的呵。
张:呵呵,是吧。我觉得中国缺的是精神贵族。什么是精神贵族,并不是说又有钱又有精神的就是精神贵族,相反的,而是说他不是把精神都放在金钱上,而是放在真正的优雅的生活方式上,放在艺术上。现在我看有些绘画为了赚钱为了惊世骇俗,就弄得特别可怕特别恶心,他的意思就是因此我与众不同。也许是我老了,从我古典美术观的角度,觉得美术它得美。艺术源于人类在劳动以后对美的需求,我还在那个阶段,他们比我进步多了,我还在那个位置上就是了。
我给自己定位是新文人画
报:您平时画的画属于什么类型。
张:我自己的画被国内一些朋友定位装饰绘画,当代艺术的一种。
报:您的父亲是个画家,他对您的绘画肯定有影响吧?
张:我父亲画画有几个阶段,一个阶段画漫画,是为了抗日或为反将服务,后来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包装新中国,就参加了国徽、政协会徽之类的设计。后来,我爸爸真正想在绘画上有突破的时候,做了一个阶段的尝试,当时华君武开玩笑是说他的画是毕加索加城隍庙。那时候,我爸画的是变形的不是视觉意义上的变形的,而是艺术角度所说的“非写实”就一定会变形。他那阶段他的探索发展得很好。可正好开始文革了,那条路就被堵死了,当时父亲受的打击比较大了。文革后,一方面父亲年龄大了,另一方面当时他不想用颜色了,就开始用画焦墨山水,全是黑的,全素的。所以美术评论家刘骁纯就对我说:“你爸爸画着画着就转型了,那条路走下去非常好,可惜文革就断了,而你现在正好走上了他原来那条路了。”但有所不同的在哪里呢,美术和文学行家分离的越远越好,意思就是,你是造型艺术,不要在里面讲故事,画画呢就是纯视觉,文学呢你就是纯文字不要弄什么诗里有画。而我呢,我爸爸是画画的,我妈妈是写作的,这个纠结我摆脱不了,所以我画画必须配文字,我自己给自己定位为新文人画。因为文人画都有故事或意境,是用形象来表述。说起这个,南京有些人早就画了新文人画,实际上是模仿清朝末年的文人画来画。实际上这个和现代没关系,我这和他们有区别。我画的画是现代的,有现代文学的语言加现代的艺术形象。当然,也有人建议我像几米那样画绘本。
报:特像古代文人呵呵
张:哈哈
报:像国画,我们平时看画可能只去注意画面,而忽视了画上的文字。那些文字应该就像日记一样把他们画画时的心情记录下来吧?
张:对对,而且文字与画面中间那个空间形成了个场,关键是那个场,让文字与画面交相辉映。文人画的要害就是在这儿。这跟现在流行的文人画不同,现在的文人画都是用过去别人的诗写用在自己画上。现在国画的创作性的确不够,到展览会,到拍卖会,你在远处一看,都长得差不多,很少人有自己的风格。
报:您的另一个身份是美术评论家,对现在的艺术评论您怎么看?
张:实际上艺术评论是受很多限制的,第一是有商业目的;第二美术评论家为了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亩三分地就得想出自己的绝招。所以说你要去双年展就得按照人家的标准,美院有美院的标准,宋庄有宋庄的标准。其实这就离开了艺术评论的特立独行美学精神了。实际上,文化的商业化以后,我们高水平的独立评论的就很少了,变成稀有的。刘小东出画册的时候,选评论他的文章就选了我的。倒不一定是我写的好,而是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不认识他。据说很多评论是有价评论,这样来说,评论的客观性就打问号了。我早知道应该问刘小东要一张画,哈哈。
报:像当年的印象派、野兽派都是评论家骂出来的吧?
张:对,实际上评论家就是批评家,你看不懂觉得幼稚的地方就该批,这样是对艺术家很好的,这样可以磨砺他啊。
报:艺术评论要比文学这类的评论热得多了。
张:这是当然的,因为这直接跟他商业价值大有关。一张画能卖几千万,一个电影几亿,里面有很大的利润。
报:这是一种商业渗透吧?
张:这和中国的商业发展阶段有关吧,处于丛林规则时代,一切都是商业化,而国外可能分工更清晰,你是艺术家就是艺术家,艺术家本人不管怎么赚钱,怎么赚钱是画商的事。这个现象并不奇怪,过了一段历史阶段自然就会好些。所以现在你能静下来去做些事,等他们回来找的时候,你不就已经走在前面了吗?我就是这么一种乐观心态。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zmf.cc/a/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