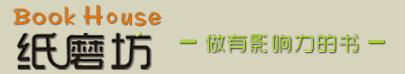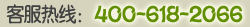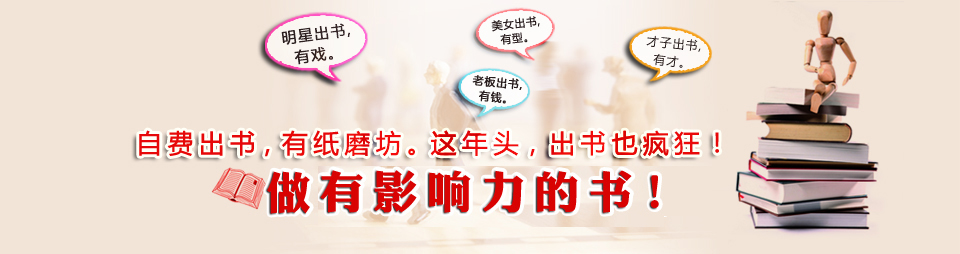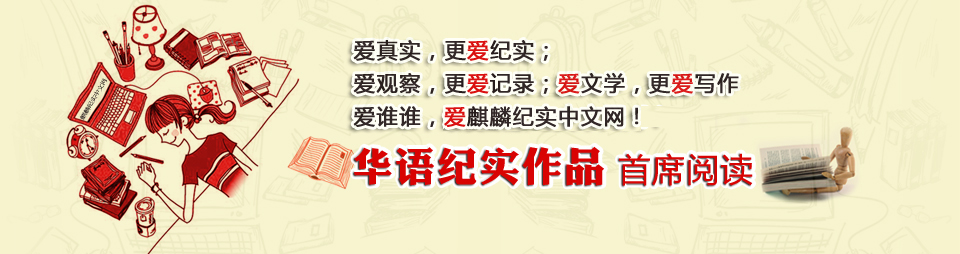“两刊”之争游戏规则,可以变一变了?(图)
发布时间:2012-09-24 09:44 作者:孔令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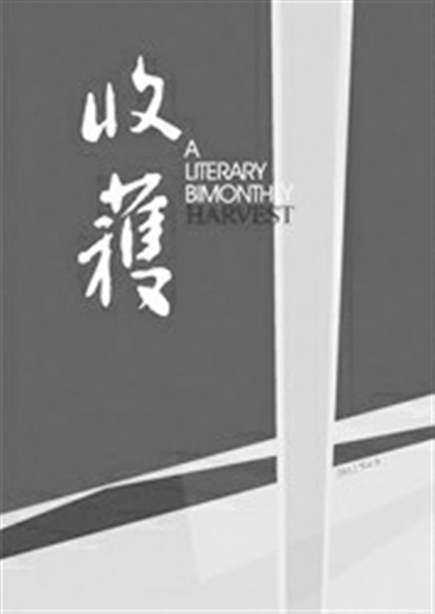

9月12日看来是个宜休战的日子。这天晚间7点多,先是《小说选刊》杂志的官方微博发出一条“郑重声明”,称“从现在起,结束与《收获》的一切争论。”5个小时后,《收获》官方微博也发出一条“郑重声明”,宣布已经上市的今年第五期《收获》中所有作者都授权他们拒绝转载。这意味着,黄永玉、叶兆言、颜歌、徐则臣、盛可以、张辛欣、南帆、陈国富等作家放弃了他们发表在这期《收获》上的作品被各类文学选刊杂志选载的机会。
不管怎么说,两本堪称在文学界跺跺脚都能震下一大片瓦当的重量级刊物——也许说彼此之间势均力敌也不为过——以各自的方式结束了这一轮口水仗。兀自留下双串渐行渐远的脚印。只是,他们终究还要再相逢,因为同在一块奶酪里,已没有太多转身空间。
事件回溯:《收获》想要修改游戏规则>>>>>>
今年五月,《收获》宣布从第三期开始,在原创作品“保护期”内,谢绝选刊物转载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此举甫出,引起热议一片。赞同者认为与时俱进的行业版权保护规则将有利于文学原创的繁荣,反对者认为杂志以“拒绝转载”的强硬方式“维权”有欠考虑,因为文学作品毕竟不等于一般商品,它天然地要求更广泛的传播和更多的读者,尤其在信息时代,“关门”一举简直是螳螂挡车。还有一拨观望者,他们更为关心读者和作者的利益,有人担心《收获》是否有“绑架”作者之嫌,“拒绝转载”是否真实地体现了作者的意愿。
刊物的执行主编程永新表示,目前不少文学选刊已演变成侵犯知识产权的客观存在。例如马原的长篇《牛鬼蛇神》,在《收获》上首发之前经历了编者与作者双方两个多月的修改完善,一旦发表,选刊类杂志付一百元左右的转载稿费就“摘果”摘掉了。更恶劣的是目前没有原创保护期,这个月发表的原创作品,下个月就可能被选刊杂志全文转载,两者几乎是同时出现在市场上,形成不公平竞争。
程永新提出:“我们只想在《著作权法》允许的框架内,维护原创刊物的一点点尊严和权益。选刊起码应该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征得作家和原创刊物的同意;2,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差。3,提高作家和原创刊物的转载费。这三点不过分吧?”
九月初,国内文学选刊类期刊的代表之一《小说选刊》杂志的主编和编辑等先后接受不同媒体的采访。主编杜卫东说,《小说选刊》即使在经济十分窘迫的情况下也按照千字40元的标准支付了稿费,经济条件有所好转之后已把标准提高到了千字50元。他们对原创文学期刊编辑的努力和贡献心怀敬意,但实在无法在稿费上向《收获》看齐。编辑部主任王干则表示:“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在作者手上,我们只要和作者打招呼并支付稿酬就已经尽了义务了”,“其实这几年我们选刊过得也很艰难,真正占了便宜的是网络盗版。这个大问题不解决,就算把全国的选刊都关了,《收获》的发行量也不会增加1万份。”而编辑鲁太光很不满意“摘果”这个说法,他认为“果子”——“作家的作品”也是心甘情愿被“摘”的。“在当前的文学形势下,选刊在推介作家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作家希望转载也有情理之中。”他还透露,“我们的确只有几个编辑,但并不等于我们就偷懒,我每月集中阅读的十多天里基本不做饭,而是叫外卖,阅过的中短篇小说不少于150部,不低于200万字。”
针尖对麦芒,谁也说服不了谁。
选刊最不想改变的恰恰是游戏规则>>>>>>
按照程永新的说法,早在上世纪80年代,《钟山》杂志就不满于选刊的做法,欲形成原创类文学期刊的同盟,保护自身利益,但被《中篇小说选刊》成功“调停”。自那时到现在,一些选刊保留了在支付作家转载稿费的同时也向原发刊物支付500元到1000元不等的转载费的习惯,有更“厚道”一点的,还会在选用的小说被影视公司看中买走改编权后想到“追补”原发刊物1000到2000元左右的“奖金”。但更多的是低稿酬(甚至不主动索取就不给)、不告知(既不通知作家本人也不告诉原发刊物)等做法。有些选刊一边哀叹经费有限,稿费只能薄奉,一边又鼓吹杂志社员工年薪五年内上涨三倍的政绩,让人闹不清到底是差钱还是不差钱,或者差的只是给作者的钱。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记者了解到,最让原创刊物接受不了的是“发表”和“选用”这个过程竟然演化成“可逆”的。一些作家会先把稿件给选刊看过,选刊的编辑决定“选用”后,便给原创刊物的编辑打电话:这个小说我们下一期要选,你们赶紧发了吧。
这样的电话,如果不是打给《收获》而是打给一本平台影响力有限的省级刊物,或者一本由政府拨款的、发行量较小的文学杂志,并不会激起反感,可能还会得到感谢。《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长篇小说选刊》等知名文学选刊之所以腰杆挺得直,和稿费的多寡没有半毛钱关系,而是他们怀有金钱难以衡量的东西。长期以来在各级相关部门都有一条规矩:原创发表算一次成果,被名牌选刊“选用”又算一次成果。一家由中国作协主管的大型文学月刊的编辑对记者表示他们是很愿意作品被选的,因为能体现工作成效,作者也高兴。
除此之外,几乎每个选刊类杂志都承担一个全国性的奖项的组织筹办工作,参评作品大量地来自转载发表在选刊上的小说。作家,特别是还未成大家、名家的作家,甘愿拿那么一点“不够买眼药水”的稿费,趋之若鹜地想要拿到一张“入场券”,也就不难理解。
“这种畸形繁荣是权力来带的利益。”一位资深文学编辑直言不讳地说。他告诉记者,这种“选”权力是可能滋生文坛腐败的。往浅了说,一个并不够份量的作品,和《收获》、《人民文学》等刊物从选用出来的作品登上了同一期选刊,就把前一个作品“拔高”到了与后者们相当的水平线上。往深了说,一些刊物自己设的奖,奖项泛滥成灾,当中如果夹带着令人不齿的交易,是无法监察和防范的。
更让人担忧的是选刊的“口味”。因为被选刊选用很“重要”,久而久之它的习惯喜好将引导作家们在无形中塑造一批近似的文学作品。“我们审稿看到一个作品的时候,就会知道它必被选刊选用,”这位编辑笑着说,“各个选刊虽然趣味有差异,但都比较重大众化,故事性,社会性。就小说叙事和语言上,相对没那么丰富。文学性强的小说是不会入选的。这样的后果是会倡导一种功利化的写作。官场小说的流行就是这样兴起的。”
《收获》:冰心老人心中的红玫瑰
《收获》杂志创办于1957年,创始人是巴金和靳以。它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大型纯文学期刊,2011年3月,《收获》杂志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冰心老人称《收获》是“心中的红玫瑰”,冯亦代先生说《收获》是“今日中国最具水准的一本文学杂志”。不少现已成为文坛中坚力量的著名作家,就是先在《收获》上亮相,然后在全国崭露头角。《收获》由此被称为作家们成名的阶梯,成为海内外了解中国文坛发展态势的一个重要窗口,甚至有评论认为,《收获》见证着中国当代文学的起起伏伏,可谓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
《小说选刊》:茅盾亲笔题名并撰发刊词
《小说选刊》创刊于1980年,图书发行《发刊词》系茅盾亲笔撰写。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zmf.cc/a/336.html